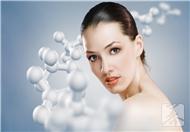人吃五穀,對於現實生活中的我們而言我們生活於俗事之中,難免有煩心之事,難免有想不開之情懷。特別是在受到他人語言攻擊或者遭受不公平的待遇時,難免會抑製不住內心坑崩潰的心理,於是生氣,甚至氣得全身發抖。這分明是拿別人的錯誤懲罰自己,那麼生氣時全身發抖是怎麼回事呢?

13年前,與鄰居紛爭,被拳腳相贈,興訟又敗北,怒氣填膺,當晚全身顫抖,頭及上肢尤甚,每隔一兩小時顫抖一次,約半時方止。天陰或驚氣時尤為明顯。求治四方,無寸效,遂萬念俱灰,自認非藥可治,幾年間不再求醫。近複因生氣而病腹痛,遂來門診。
望其麵色微青,頭與手不停搖抖,舌淡紅潤,舌苔薄白。詢知胸脅苦滿,飲食不思,惡心欲吐,口苦,不思飲,大便正常,小便時抽引少腹疼痛。日暮寒熱,易驚悸,夜寐差。月經正常,帶下較多。腹診心下無壓痛,兩脅下有抵抗,右側尤甚,當臍悸痛。切得脈象弦細。
觀其脈症,知腹痛為甲木犯土,肝胃不和。其舊病亦為七情所致,怒氣傷肝。《素問•舉痛論》雲:“怒則氣上。”《素問•至真要大論》雲:“諸風掉眩,皆屬於肝。”掉者,搖也,即顫抖也,屬肝木風動之象。今肝木橫逆,腹痛陣陣,治宜舒肝和胃,緩急止痛。至於夙疾,伍以鎮肝熄風,亦不悖方意,豈非一石二鳥!

擬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加減:柴胡12g,黃芩10g,半夏10g,茯苓15g,川軍6g,桂枝6g,龍、牡各30g,白芍15g,甘草6g,二劑。
二診:藥後泄瀉數次,腹痛愈,嘔惡不再,心悸止,夜能安臥,十餘日中顫抖僅發作一次。病者乞漿得酒,喜出望外,得隴望蜀,更求絕顫,付與原方三劑。
三診:月餘未顫,詢問需否用藥?餘診畢,未予書方,告之知足不爭,大度寬容,乃根治之良方也。
按:13載,首為之搖,手為之舞,且不言身軀之痛,就路人之注目,左右之指點,內心之苦楚亦已飽嚐。今求治腹疾,服藥五劑,曆時一周,竟使陳年之疾亦愈。病者樂,餘亦樂。
李映淮老師評語:振顫乃肝之病,風之象,為棘手之症,臨床以虛及虛實夾雜證型為多,實證較少。本案為肝火風動,非陰血虛弱之肝風,故短期而愈。

原文複習
《傷寒論》第107條:傷寒八九日,下之,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譫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主之。
各家論述
《傷寒來蘇集》:取柴胡之半,以除胸滿心煩之半裏;加鉛丹、龍、牡,以鎮心驚,茯苓以利小便,大黃以止譫語;桂枝者,甘草之誤也,身無熱無表證,不得用桂枝,去甘草則不成和劑矣;心煩譫語而不去人參者,以驚故也。
《醫方集解》:柴胡湯以除煩滿,加茯苓、龍骨、牡蠣、鉛丹,收斂神氣而鎮驚;而茯苓、牡蠣又能行津液、利小便,加大黃以逐胃熱、止譫語;加桂枝以行陽氣,合柴胡以散表邪而解身重,因滿故去甘草。
《古方選注》:柴胡引陽藥升陽,大黃就陰藥就陰,人參、炙草助陽明之神明,即所以益心虛也;茯苓、半夏、生薑啟少陽三焦之樞機,即所以通心機也;龍骨、牡蠣入陰攝神,鎮東方甲木之魂,即所以鎮心驚也;龍、牡頑鈍之質,佐桂枝即靈;邪入煩驚,痰氣固結於陰分,用鉛丹即墜。至於心經浮越之邪,借少陽樞轉出於太陽,即從茲收安內攘外之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