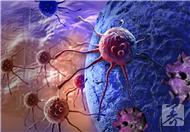上周,聖地亞哥市迎來“同誌驕傲周末”,我前往跨性別群體中心做誌願服務。我向兩個接待員做自我介紹,表示想為同性戀青少年做些事情。“我想組織一個青少年寫作社團。讓他們講述自己的故事。我想讓他們在最痛苦最黑暗的時刻也能看到光明。”我如此說,接待員卻興趣缺缺,好像完全記不起童年,或從沒經曆過身為社會邊緣人的痛苦。我繼續闡述我的想法,試圖打動他們,可他們卻連與我對視的工夫都沒有。一個接待員好心地提醒我,青少年根本不被允許進入主會場。他指著南邊,示意我去青少年會場。我拿到青少年會場的聯絡人的名片,就此離開了大廳。我疑竇滿腹。青少年是多麼敏感的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有人傾聽和關注是多麼重要。我無法理解我們為什麼忘記這一點。
我想起自己黑暗的少年時期:深刻的絕望,自覺罪孽深重;沒有人可以傾訴和求助,仿佛被全世界拋棄。我想起了我寫的那些自殺紙條,信手放置在某個地方,等待被人發現。紙條是我計劃的第一步。第二步,是為付諸實施的自殺。我想重提這些事情:
“親愛的朋友:”
我的自殺紙條是這樣開頭
那些被揉皺
放在浴室的籃子裏
扔在我床下
布滿灰塵裏的紙條
“親愛的朋友,”我在紙條上這樣說……
“每一個
曾友善待我的人
不取笑我怪異的人
我希望你們了解
我是束縛在女孩身體裏的男孩
我的死亡
不是你們的錯”
我不想讓他們難過
盡管我不得不離開
因為我的出生是個錯誤
我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
“是那些在突然攻擊我的男孩
他們對我又捶又揍
直到我幾乎無法走回家
是那些熱衷秘密的女孩
她們在野餐會上躲著我
我找到她們時
一整籃三明治
沒有一個人吃
我的離開
不是為了苛責或懲罰
我是個錯誤的產物
並且無法修複
我披著女孩的身體,卻有一個男孩的靈魂
我是自然的怪物
我是上帝的錯誤”
10歲的我忍住淚水
寫下這些紙條
我努力變得勇敢
把話說得清楚明白
我渴望被人看見
卻無人看見
更無人理解
真正的我
他們隻知道按我的外在
區分我的性別
半個世紀後
我身體裏的男性和女性
終於握手言和
我感謝照拂我的那顆幸運之星
讓我不需要在家裏準備割腕的刀片
不需要依賴毒品逃避現實
不需要物色適合跳崖的絕壁
也不需要尋找適合斷頭的鐵軌
我時常會想
是否有人
看到過我當年寫下的紙條
然而從未有人
以此詢問過我
這個問題十分嚴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