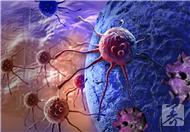抑鬱症是很複雜的。作為一個非專業人士,我隻能根據我的經驗來談談抑鬱症。

我要談的內容不是基於各種實驗或廣泛閱讀文獻評論,而是基於我20年與不同程度抑鬱症打交道的切身體會。在大學期間,我的抑鬱症第一次發作。那種感覺就像雪崩一樣。生活像雪球一樣滾著,事情隻是表麵看起來好罷。那時候,有男朋友、高GPA、好朋友、好的音樂以及歡聲笑語。但是我跟男朋友的關係開始惡化(是我個人原因,與他無關),這個事實讓我變得很傷心以及疲憊。我很多天都不想吃飯。我隻需要一天15-20小時的睡眠。“分手憂鬱”是生活中正常的事,不是嗎?不正常的是——我不能從中恢複過來。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的病當然獲得了緩解。但是抑鬱症是一種要麼會複發要麼就一直得到緩解的慢性疾病。就像多發性硬化症、糖尿病和囊胞性纖維症一樣,你會感覺幾個月乃至幾年抑鬱症好像好了,但是如果你放鬆警惕,你的抑鬱症仍存在複發的危險。
抑鬱症也像其他疾病一樣,在不同人身上表現的症狀不一樣。一些人的症狀是很明顯的。他們的傷心是可以看出來的,看著他們自己也覺得難受。他們有著拖曳的步伐、空洞的眼神、髒兮兮的襯衫以及沉重的四肢。他們看起來就像正在流沙地行走一樣。毫無疑問,他們患上了抑鬱症。他們需要醫療照顧。他們可能痊愈、也有可能不會痊愈。因為遺憾的是,就像任何一種慢性疾病患者——一些人進行治療(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後痊愈了,一些人卻沒有。就像任何一種慢性疾病患者,一些人會因為這些病而死去。
在我在貝爾維尤醫院的時候,我見到一個很親切的男人,他這些年斷斷續續地進醫院好幾次。他剛好沒多久又因為複發而進醫院。精神病醫生告訴我他的病到了末期,但讓我困惑的是那時他看起來很健康。醫生解釋道這個病人已經用過市麵上全部的抗抑鬱劑,也進行過好多回合的電驚厥療法。他的病很難治,很難痊愈……他的病已經到了末期。他最終會死去,什麼時候死去就未知。
抑鬱症可以很難以捉摸。因為你表麵可以看起來很正常、很高興,你甚至可以微笑。你可以上班並且完成工作。你可以去雜貨店、寫一份方案、駕駛汽車、提交一份研究計劃以及拖地。你可以鍛煉、照顧嬰兒、解複雜方程式以及平衡你的收支。你可以經常笑。你可以去購物,並且狀態看起來很好。但是實際上你仍然在心裏過著與其他正常人不一樣的生活。
你不確定你知道怎麼再真正的高興起來,甚至是真正的傷心、憤怒以及焦慮。你變成一個上好油的機器,知道怎麼做卻不知道如何去感受。
煩躁不安是不舒服和不高興的綜合。這個詞來自希臘——它的意思是“難以承受”。這個詞描述這種抑鬱症很恰當。這種抑鬱症很難卻不是不可能忍受。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看起來很正常——因為這不是流沙抑鬱症,症狀很明顯。患這種抑鬱症的感覺就像走在海藻裏——艱難卻不是不可能。
這種抑鬱症,如果一直保持這種狀態,是不會讓你死亡。但是它會奪去你的歡樂、與他人聯係以及腳踏實地的生活的感覺。它會讓你漸漸失去自己的人際關係和善良。
很幸運,我沒有患上流沙抑鬱症和抑鬱症末期,我很感激造物主給了我好的DNA,也感激找到血清素、多巴胺以及能治療我的病的藥物。我更感激那些藥對我有效。這是我非專業的觀點——這是我與羅賓·威廉姆斯和其他每年死於流沙抑鬱症的人的唯一區別。我的病是有藥可治的。或許他們的病不是。
因此無論是患上了流沙抑鬱症還是海藻抑鬱症亦或者是兩者的結合(我稱其為流沙海藻抑鬱症),我希望患者都能勇敢地說:“我患了流沙抑鬱症,請幫幫我。”我們會理解的。因為病人不必為疾病感到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