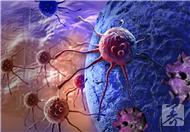瑪麗亞.斯是一名博士,專門從事神經心理學,同時還是一名科學家,心理學家從事於美國德克薩斯州達拉斯的學術醫療中心的。當她對待病人,評估認知功能就是她的工作,因為這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意味著思維和記憶。有時候,她也要診斷抑鬱症患者,他們會伴有憤怒,懷疑和否定的混合反應。她想對她的病人說她就是臨床抑鬱症的幸存者。
通常情況下,我會有一些病人在他們50多歲和60歲的時候會開始關注老年癡呆症。他們進來,很肯定自己有癡呆或覺得他們記憶退化了。
我告訴他們,“是的,我從在你那收集的數據來看你確實是有點問題,但我覺得那不是老年癡呆症,而是抑鬱症。”
以我個人來說,這是非常好的消息。我很激動的告訴他們他們沒有患癡呆症,因為老年癡呆症是不可治的。但這也有點令人沮喪,當病人們知道自己得了抑鬱後會感到很失望。因為我就是帶著抑鬱症生活的,所以我知道這是不致命的也是可治的,而且你可以存在的很有意義。但當他們把這想象成和老年癡呆一樣或甚至更糟的病時,那這就會變得很艱難。
有點困難的是我的雙重位置,是的,我即是一名醫生也是一個病人。你想透露給你的病人的一定不是 -“我知道這是很有效這對我很有用。”的說法,因為心中很鬱悶,所以實際上可能會把你的話扭曲為“嗯,你鬱悶,所以你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我現在恢複的很好,而我試圖讓人們好好利用可用資源。因為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 - 我們擁有一些過去沒有的資源。
我第一次意識到我需要幫助實在上大學的時候。我發現自己在受虐的關係中,我到處尋求幫助以擺脫這種關係。所以,當我的治療師幫助我那段關係後,她也表示擔心我可能會患上混亂臨床抑鬱症。我很同意她的觀點。
我被確診時我才20歲,但我記得那段小孩子難以承受的悲傷的時期。那是我第一次有這種感覺,特別是那厚重的悲傷的感覺,還並沒有消失 -顯然我仍然記得這一天,對我這樣的孩子來說那是一個大問題 -那天我最好的朋友決定,她不想和我一起玩。那個時候我才5歲。我很難接受這個消息,但回過頭去看,我比我想象的中更加努力的想要去接受這個事實。
當我告訴我的母親我的診斷結果時,她難過極了。她說,“這真是是一場噩夢。”
那個時候是在我自己國家,我第一次抑鬱發作,我想,“好吧,想象一下我會是什麼樣子。
我的父母是新奇的一代,他們都非常崇尚白手起家的心態。因此,他們不明白為什麼我不能感覺好一點。奮鬥了幾年後還是那樣,也就是20年後,我仍然覺得自己在努力教育他們- 不隻是關於抑鬱症是什麼,還有關於對我來說抑鬱症意味著什麼。這是種永遠不會結束的教育。
對我來說,抑鬱症是我實實在在地感受到的胸上的負擔一直延續到手臂。我已經知道這種感覺了。我想,如果你有一個以上的抑鬱發作經曆,那麼你就可以開始注意到這些跡象了。
這是一個非常朦朧的感覺,就好像你正在與世界上其它黑暗的隧道的人進行通信,你呼喊,試圖與人溝通。你不一定完全理解別人和你所說的。從邏輯上講,你理解。但你稍微慢了一點。
我知道我很容易抑鬱發作,我努力采取措施以避免它。我知道一些會有幫助的方法,盡管我不喜歡做-運動,與其他人交往。但每過一段時間就不管用了,然後我的情緒就會低落兩個多星期,我會感覺昏昏欲睡。然後我就會吃藥,表現的和往常一樣,然後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用著些可能會再用到的知識生活,我覺得並沒有和別人想象的一樣痛苦,因為你了解了讓它好轉或轉壞的模式。你熬過的次數越多,你感覺到的生存幾率就越大。
這有一種抑鬱症很受用的思想。所以,我試圖讓我自己的思想有用。當其他人在鬥爭時,如果他們是我的朋友,我會說,“我也在戰鬥。”